作者:尚权律所 时间:2021-08-1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风险社会与刑法立法科学化研究”(16CFX023)阶段性成果。
引言:涂鸦惹祸,艺术难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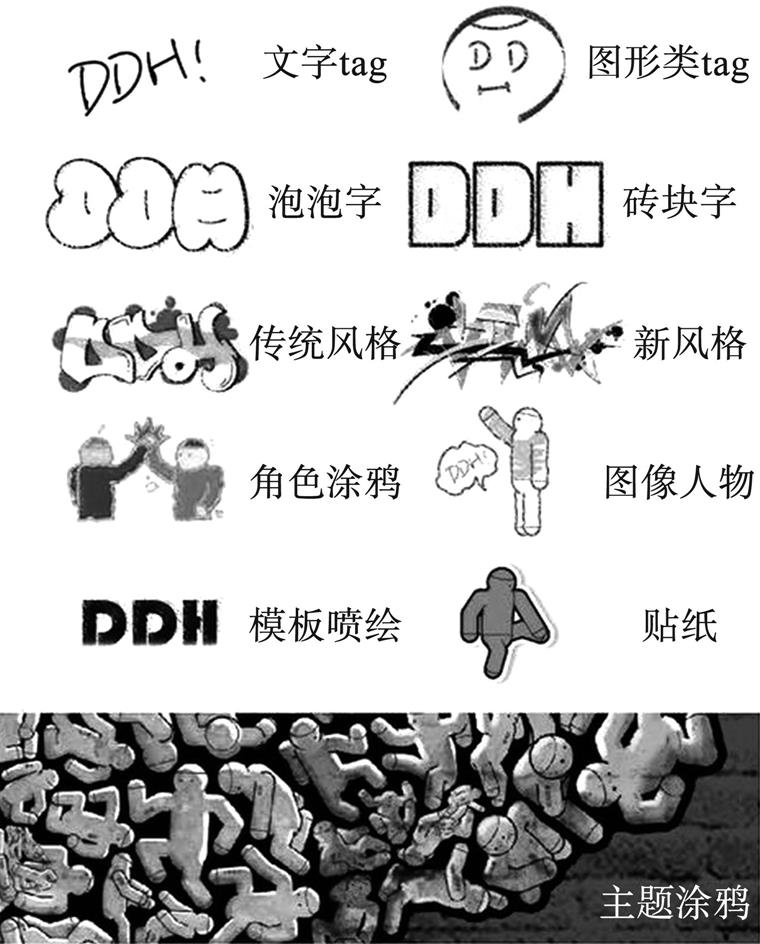
图1 涂鸦分类示意
资料来源:帝都绘制作,微信ID:diduhuiBJ。
(一)喷漆
(二)小广告
(三)乱写乱画

图2 厦门大学芙蓉隧道内的乱写乱画
法条与案例:基于域外视角的考察
(一)英国
(二)美国
(三)法国
(四)德国
(五)日本
(六)新加坡
(七)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图3 法国涂鸦艺术家Zevs在香港特别行政区Giorgio Armani专卖店外墙上的涂鸦
(八)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九)中国台湾地区
涂鸦何以为罪:对“财产说”的质疑
(一)外观是否属于损毁对象?
表1 外观变更行为可罚性类型化分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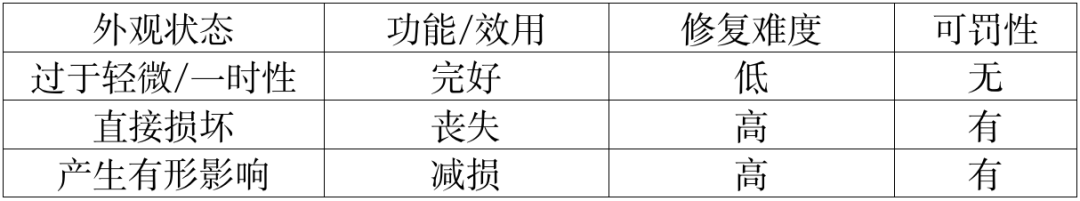
注:参见张梓弦:《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有形的影响说”之提倡》,载《法学》2018年第7期。本表系笔者根据其观点绘制而成。此处的修复难度可从时间支出、劳力支出和费用支出三方面加以理解。
(二)损毁程度有无要求?
(三)外表美观是否属于客观效用?
 图4 北京喷子(BJPZ)涂鸦团队作品
图4 北京喷子(BJPZ)涂鸦团队作品
图5 观音涂鸦团队作品
涂鸦何以为罪:对“秩序说”的批判
(一)冒犯行为需具有严重性
(二)观者合理避开冒犯场景的难易程度
(三)冒犯行为本身不具有合理性
(四)被冒犯者的反应是理智的

图6 KTS涂鸦团队成员爬上空调外机创作Tag涂鸦
罪名适用之困:兼对“林欧案”的简要评析
公共空间的话语争夺:作为都市问题与破坏主义的涂鸦
对此,可从以下几个视角予以理解。
(一)反叛与发声:作为“空间生产”的涂鸦

图7 要停车,还是公园,这是个问题(英国涂鸦艺术家Banksy作品)
(二)治理与管制:作为“都市问题”的涂鸦
1.追根溯源:涂鸦何以成为城市顽疾?
2.他山之鉴:反涂鸦战争的“纽约经验”
 图8 纽约地铁车身涂鸦即景
图8 纽约地铁车身涂鸦即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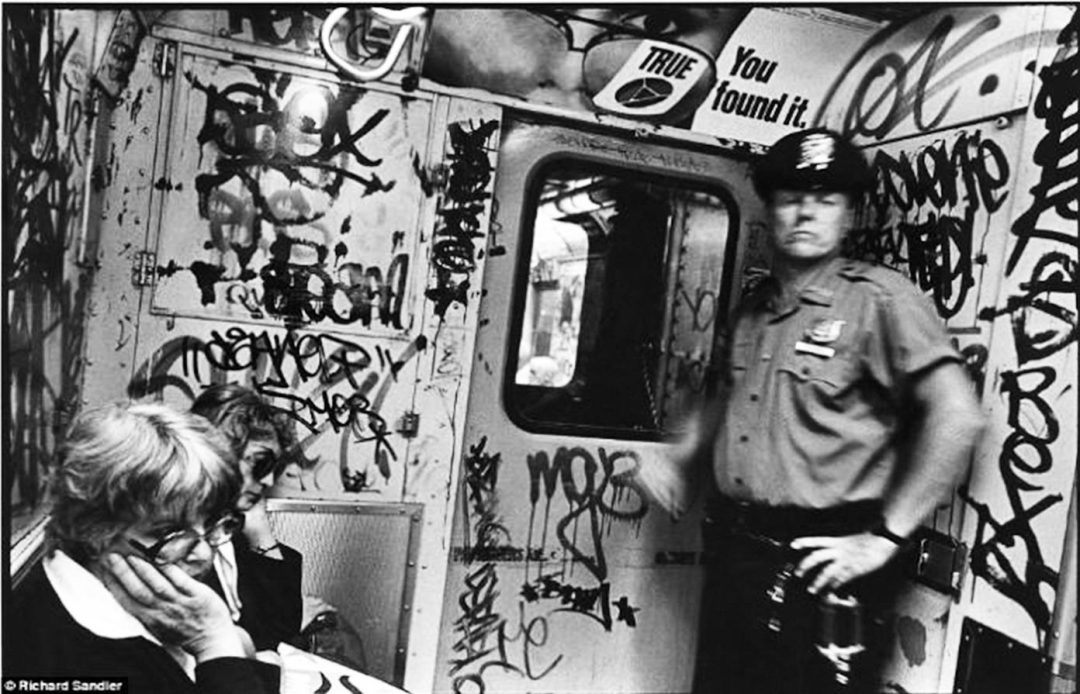
图9 纽约地铁车厢涂鸦一瞥
3.治理反思:“新军事城市主义”的失灵

图10 早期为防治涂鸦者侵入的纽约地铁沿线铁丝网
(三)失序与非法:作为“破坏主义”的涂鸦
1.“破窗理论”视角下的涂鸦
2.亚文化视角下的涂鸦
结语
 图11 涂鸦团队就社会热点问题发声
图11 涂鸦团队就社会热点问题发声
图12 北京喷子涂鸦团队涂鸦作品《众志成城》(局部)
来源:《法律和社会科学》法律、城市与地理(第18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21年出版。
作者:刘炯 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