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权律所 时间:2023-07-05
前文回顾:
尚权研究丨赵正武:刷新对《武汉会议纪要》最后一条的理解 ——在药品犯罪新司法解释施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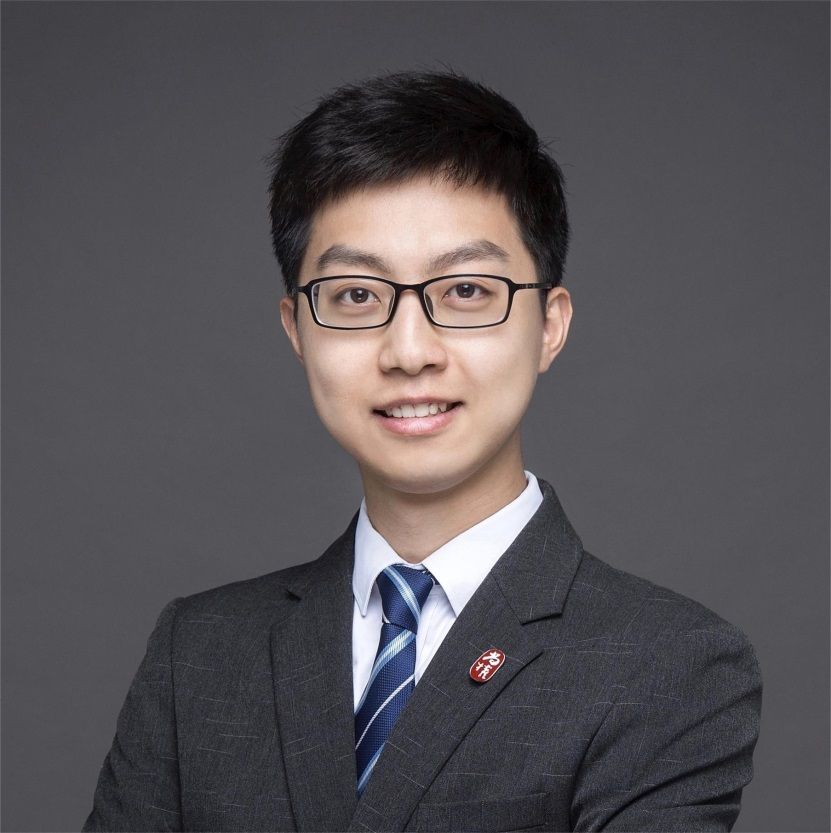
赵正武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经济犯罪研究与辩护部副主任
武汉大学刑法学硕士
话说行为人郑某经过辩护律师一通化腐朽为神奇的辩护操作,被法院判决无罪。从看守所出来后,郑某又回到手工装配厂上班,天天装扣子。不知道是因为刑事程序的几轮折磨,还是天天流水线作业转坏了脑袋,郑某的精神好像受到了刺激,总觉得小芙变得怪怪的,不像从前那么爱自己了。而且,郑某还不时会看到隔壁车间的王生来找小芙聊天,一看到自己就又马上离开。郑某疑心,王生和小芙之间肯定有事情!难怪王生车间那几个男工一看到自己就怪笑,问他们,又神秘兮兮的,不响。
一天,郑某偶然又看到王生和其他同事在欢快地聊着什么,好像在谈论小芙的习惯。郑某气急败坏,回家质问小芙,自己不在家时是不是跟王生好上了?!小芙错愕,骂郑某有神经病。郑某空口无凭,摔门而去,到大街上转圈,还是越想越气,便又买上水果刀,骑上电动车,一路找到王生的小区,正好撞见王生回来——
从小区监控录像看,郑某在晚上20时14分,与王生相向而行,迎面捅刺王生多刀,随后被小区邻里发现。事发后,郑某一直站在现场血泊中,直到被赶来的民警控制……
公安随即对郑某进行了密集侦讯,郑某在前6次讯问笔录中,都稳定地供述,自己因怀疑王生与妻子小芙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盛怒之下,找到王生用刀故意杀害了对方。但是,或许是出于求生本能,或许是被同监室人员鼓动,也或许是如实交代,总之,郑某在第7份讯问笔录里,突然提出要求,申请对自己进行精神病鉴定。郑某表示,自己当天在到达王生所在小区后,脑子里充斥着曾经看过的电影画面,觉得有一股力量在牵扯着自己,随即他看到了正步行回家的王生,突然,好像有一阵黑影朝自己扑来,之后就什么也记不清了,等自己反应过来时,已经被带到了讯问室,才意识到自己造成了王生的死亡。郑某怀疑自己有精神疾病,导致自己在当天傍晚意识混乱、行为控制能力减弱。
郑某杀了一个人,整个过程被小区监控摄录下来,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可能救郑某命的,除了精神病鉴定,就是自首的认定问题。在目前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下,死亡一人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情节时,有一定几率能够保命。
一审法院认为,郑某在作案后明知他人报警,仍于现场等待抓捕,可视为自动投案;而郑某虽然承认王生的死亡是自己持刀捅刺造成的,但其辩解见到王生时感觉有一阵黑影扑向自己,之后的事情都记不清了,是“否认了其具有辨认、控制的刑事责任能力及其主观上有杀害王生的直接故意”,因此,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构成自首。郑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即上诉到二审法院。
那么问题来了,暂时抛开同样重要的精神病鉴定不谈,仅就自首认定问题而言,本案中,郑某的行为究竟应当认定自首吗?
本文认为,郑某依法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具备自首情节。具体论述及延伸思考如下:
一、郑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其最后一份讯问笔录中的辩解属于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依法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关于何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除了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的解释——“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表明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是要如实供述“全部的”犯罪事实外,历来在是否能客观主义地解释“罪行”上,也存有争议。
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该《批复》的理解与适用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祝二军也明确:“该两个要件(指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从性质上看,属于客观要件”。(祝二军:《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2004年第2集,总第37集。)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解读此《批复》时也曾指出:“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属于被告人主观方面的内容,与自首成立的上述客观要件无关,因此,不影响自首的成立。”这说明,当被告人在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客观行为以后,在此基础上,对自己行为的定性进行性质辩解,不应当影响认定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2004年《批复》基本上对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采取了客观主义的解释立场,该《批复》与相应的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被普遍地接受并适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直到现在也仍可以检索到大量相关案例。本文也认同这一认定标准,自首作为一种体现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对较低,且有助于策动被告人主动供述进而节约司法资源的法定从宽情节,原则上应当较为宽松地予以把握,而不能全面地挤压甚至实质性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
“如果认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要求被告人如实供述四要件的全部内容,那就意味着被告人不能针对上述四要件进行辩解,否则就不属于如实供述,这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聂昭伟:《被告人针对主观心态的辩解不影响自首成立》,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12月8日第7版。)
本案中,郑某在前6份讯问笔录中一直稳定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因故找到被害人王生,并持刀故意对其进行捅刺的事实经过,对于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工具、打击部位、作案动因等事实都予以了详细供述。在第7份讯问笔录中,郑某辩解说“控制不了自己”,说当时没有辨识能力,有控制能力削弱的现象。亦即,郑某辩解否认自己作案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将直接影响其涉案行为的定性——是规范上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故意杀人行为,还是事实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者的故意杀人行为——这当然属于2004年《批复》中“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因此该辩解自然不应该影响认定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进而影响自首的成立。
综上,根据《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及其理解与适用,应当认定郑某符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成立自首。
二、即便以最不利于行为人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认定标准,郑某依然符合相应条件,成立自首
在2004年《批复》生效之后,司法实践中遵从此《批复》意见,产生了大量判例,但也存在一种反对观点,这种观点并不反对2004年《批复》,而是认为2004年《批复》并不意味着被告人只需供述自己客观面的罪行,主观面的罪行也需要如实供述,只不过在此基础上,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认定自首,而已。
上述观点集中体现在2014年《刑事审判参考》所刊载的第941号冯维达故意杀人案中,冯维达案的裁判要旨对围绕2004年《批复》的一些实践解读与适用提出了批评,并就自首的认定提出了一个更严格的认定标准。其指出,被告人需要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观面犯罪事实,如果其对主观心态的辩解与现有证据所能查明的案件事实相矛盾,则不能认定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冯维达故意杀人案中,即是根据车辆撞到人之前没有刹车痕迹,来认定被告人没有如实供述已查明的主观故意。)反之,“如果行为人的辩解具有合理的根据能够成立,或者不能被在案证据排除的,就属于没有改变或者否定案件事实,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冯维达、周峰故意杀人案——行为人对其主观心态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的成立》,载《刑事审判参考》2014年第1集,总第96集。)
而在郑某案中,即便采用《刑事审判参考》冯维达故意杀人案中对行为人最不利的认定如实供述罪行的标准,郑某也仍然符合相应条件,能够成立自首。一审法院认定郑某的辩解否认了“其主观上具有杀害王生的直接故意,因此,其并未如实供述其罪行,故其不构成自首”,是错误的。论述如下:
第一,郑某从来都没有否认过其故意杀害王生的主观事实。其前6份讯问笔录的供述一直十分稳定,在此不再展开。而仔细审查郑某的最后一份讯问笔录,可以看出以下几点意思:首先,郑某表达的是,他在到达王生所在小区后,看到王生正在朝自己的方向走来,然后有一阵黑影向自己身上扑,之后脑子就一片空白了,也就是说,郑某对于作案的核心过程类似于失忆了;其次,在办案人员问郑某“你是否杀害王生”时,郑某回答后来自己到了公安机关后,就知道自己杀了王生了,王生的死亡是自己造成的,只是具体造成过程记不清;最后,这种看似有些奇怪、不合逻辑的回答,郑某的解释是,自己“脑子里有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死死地卡在我脑子里面,使我无法自拔……在路上的时候有一种力量在牵扯我,让我去找王生,我控制不了自己……”
也就是说,整体解释最后一份讯问笔录,郑某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虽然作案时“脑子一片空白”,但并不否认事后所能回想起的事实是自己造成了王生的死亡,也没有明显说自己是过失的意思,而只是一时无法控制自己,被“一种力量牵扯”着,造成了王生的死亡。
而郑某虽然在最后一份笔录里表达了自己作案时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意思,但与此同时,并没有否认其前6份笔录的内容。也就是说,其从头到尾都没有否认过自己“故意”杀人的事实。(虽然郑某在前6份笔录里没有直接说“我是故意的”,但从郑某对事实经过的描述看,“我就直接捅他了”,“我又捅他腹部一刀”等类似表述,都明显能看出是故意性意向的供述。)
那么综合郑某的7份笔录,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郑某从来都没有否认自己的杀人故意,只是在最后一份笔录里提到了自己无法控制自己,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郑某所辩解的重点是说自己无法控制自己,但那个无法控制自己的人,仍然是故意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这种辩解并不矛盾,反而非常契合一个精神疾病患者病发时的所作所为。
第二,既然郑某并没有正面否认自己的杀人故意,那么从裁判说理的行文来看,认为郑某的辩解“否认了其具有辨认、控制的刑事责任能力及其主观上具有杀害王生的直接故意”,就还存在一种可能,是因为郑某否认了自己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而被认为否认了自己的主观故意——但是,这种推演认定,恰恰在考察行为人是否成立自首的具体问题里,是一种错误的法律评价。在自首的考察中,并不能因为行为人怀疑甚至否认自己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就代表行为人连带否认了自己的主观故意。
如果一审判决果真是如此连带否定,那就犯了一个专业人士才可能出现的具有技术含量的错误。传统观点之一认为:“犯罪主体条件的具备,是行为人具备犯罪主观要件的前提,也是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能够达到刑罚目的的基础。”(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80页。)“犯罪主观方面要以犯罪主体的主观意识能力存在为前提”,(马克昌主编:《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在犯罪体系的规范结构中,刑事责任能力是每一个行为人的罪责基础,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当然也就不能成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犯罪故意。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在事实层面,就算是一个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也存在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之分,只是在规范评价的视野中,并不会再将精神疾病患者的行为评价为符合任何犯罪构成的行为了。
重点是,在考察行为人是否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否成立自首的问题上,恰恰不应该用规范评价的眼光来要求任何一个行为人,而是只对行为人在事实层面提出如实供述的要求。绝大部分的行为人,本身并不是专业的法律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在其交代犯罪事实时,不可能保证其意识到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在规范评价的意义上、在刑事入罪结构中,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行为人只需要如实交代其所知道的事实,便足矣,至于这些事实材料应该被如何整合、评价,则是司法工作人员需进一步做的工作。也正因如此,法律规范体系中才会出现2004年《批复》的类似内容,因为行为人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因此其对于自己所交代事实的性质评价,完全有可能是偏颇或错误的,但不能因为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错误认识与相应辩解便影响其自首的成立。至今仍然具有效力的2004年《批复》,其背后的法理也表明了,在本案中因为郑某否认自己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便否认其供述主观故意,是非常不妥当的,是一种错误的法律评价。
(相信我已阐述清楚,本文无意讨论刑事责任能力与犯罪故意的关系问题,而是想要强调自首认定中的评价视角。)
反过来看,如果按照上述裁判思路,实际上就是说所有认为自己作案时可能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而申请精神鉴定的行为人,都不可能符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都不可能成立自首——这是极其严苛和武断的,极度压缩了自首的成立范围,与防止片面从严、挽救大多数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是不相符的。
综上,即使是按照冯维达案所提出的不利于行为人的认定标准,由于郑某也交代了自己主观面的犯罪事实,与在案证据所查明的事实并不矛盾,且不能因郑某否认刑事责任能力就连带认为其否认主观故意,那么郑某仍就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应当成立自首。
三、发散:哪种犯罪论体系更能为思考如实供述要素问题提供启示?
回到四要件的传统视角,涵盖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要件,本来就是和客观要件分列的要件之一,如果只认为行为人应如实供述客观要件事实,那么刑事责任能力本就不在应当如实供述的范围之内。即使认为行为人也应当如实供述主观要件事实,和刑事责任能力也依然无关(如果不考虑关联性问题的话)。除非,一定要从主客观二分法来划分四个要件,则主体要件事实可能又会被划分到客观面事实之中,那么其是否属于需如实供述的罪行,则又会产生争议,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四要件的各个要件虽然在名称、在能指上带有“主”“客”这样的表述,但它显然不是按照主客观二分法所划分出来的四个要件。)
行文至此,想必已不难发现,四要件本身的划分与排布,从根本上就不适合作为思考“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应包括哪些要素”这一问题的逻辑框架。它固有的框架在这个问题上会产生一种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就是容易导致两种极端的结论——要么,只需要供述客观要件事实(显然,一部分人是不满意的,不然围绕2004年《批复》就不会产生争议);要么,就客体、客观、主体、主观四个方面的要件事实都必须如实供述(从而又会出现前文批评的剥夺辩护权等问题)。
所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应包括哪些要素”这一问题的讨论,早已脱离四要件的框架,而仅就其问题本身进行挖掘和思考。
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从阶层论比如三阶层的视角来看,就会呈现一个相对清晰的框架。无论是把“故意”和“结果”“行为”一样定位到第一阶层(构成要件层面)的某些三阶层体系,还是把“故意”定位到第三阶层(有责性层面)的三阶层体系,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把“刑事责任能力”置放在第三阶层的责任层面。“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显然只要求行为人供述到第一阶层即可,而不要求把三个阶层全都供述完毕。第三阶层是一些个别化的涉及责任有无与大小的考量因素,第一阶层才是与“罪行”最为紧密关联的内容。
阶层论本身所强调的思考的位阶性及要素分区,已经逻辑性地为需要如实供述的罪行要素给出了一种答案,或至少是启示。而这种答案,从对结论的理性检验来看,还是相对合适的。
总之,无论是从应否考虑刑事责任能力与犯罪故意的规范关系,还是从阶层论的视角来看,都清晰地表明了,不应因被告人否认自身刑事责任能力,就判定其未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四、要求行为人如实供述刑事责任能力天然存在悖论,是一种虚妄
抛开犯罪论体系,我们再来正面考虑一下,如果要求行为人“如实供述”自己的刑事责任能力,对自首制度乃至整个刑事司法而言,有何意义。
如果一味追求办案效率、强调节约司法资源,那么当然,自然是被告人对定罪量刑不作任何发难为好,不要在正常程序推进中出现任何“幺蛾子”,被告人最好是对指控照单全收。在这种想法下,当然会认为要求行为人也要如实供述自己的刑事责任能力,才会是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的(制度压力会让部分被告人打消/撤回精神鉴定申请),也就似乎和自首从宽的根据之一搭上了线。
但是,至少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理念,仍旧是首要强调实体公正,是要查清客观事实,要根据所查清的事实作公正裁判,只有在公正有保障的前提下,才适合去谈提高诉讼效率与节约司法资源等问题。
然而,在刑事责任能力这个问题上,要求行为人作如实供述恰恰是一种虚妄,其中天然存在着悖论。就像让酒鬼说自己醉没醉一样,真正精神有问题的患者,往往会认为自己没问题,不是精神病人;而部分精神正常的行为人,出于求生、求轻判的本能,或是出于某种短暂的幻觉,又可能会谎称或怀疑自己有精神疾病。到底有没有精神疾病这件事,别说行为人自己有没有认识错误问题,就连医学和心理学专家们也各有议论、莫衷一是。
而且,就算鉴定专家拍板了,也仍旧不是最后一步。归根结底,有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基于科学事实的规范评价,一种法官依靠医学上得出的鉴定意见所作出的规范判断。在这段“事实-科学-规范”的三重奏中,行为人只需要如实供述“事实”部分(自己当天到底喝了多少酒,当时大脑是不是一片空白等等),精神疾病专家来负责“科学”鉴定,最终交由法官作出“规范”判断——而后两重环节本身就颇具争议性。科学与规范评价都难以厘清的事情,要求行为人自己“如实”交代,是不是缘木求鱼、敲冰索火,深含讽刺呢?
所以,在有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上,本来就应当更多地通过外围证据事实予以判定,而行为人自己的表态,参考意义并不大。从这个角度讲,自首制度中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也毫无必要把刑事责任能力予以纳入。
五、最后一线生机
最后,还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思路是,即使类似郑某这样的行为人,在最后一份讯问笔录里提出要求精神鉴定,表示自己不记得核心作案经过,从而被认为否认了自己的犯罪故意,属于翻供,但郑某们也仍有一线生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最后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只要行为人在一审庭审中能提供解释并再次作回前期供述,或者在一审判决前通过自书材料的形式再次如实供述,确认其犯罪行为(与故意),依法仍然应当认定为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