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权律所 时间:2024-0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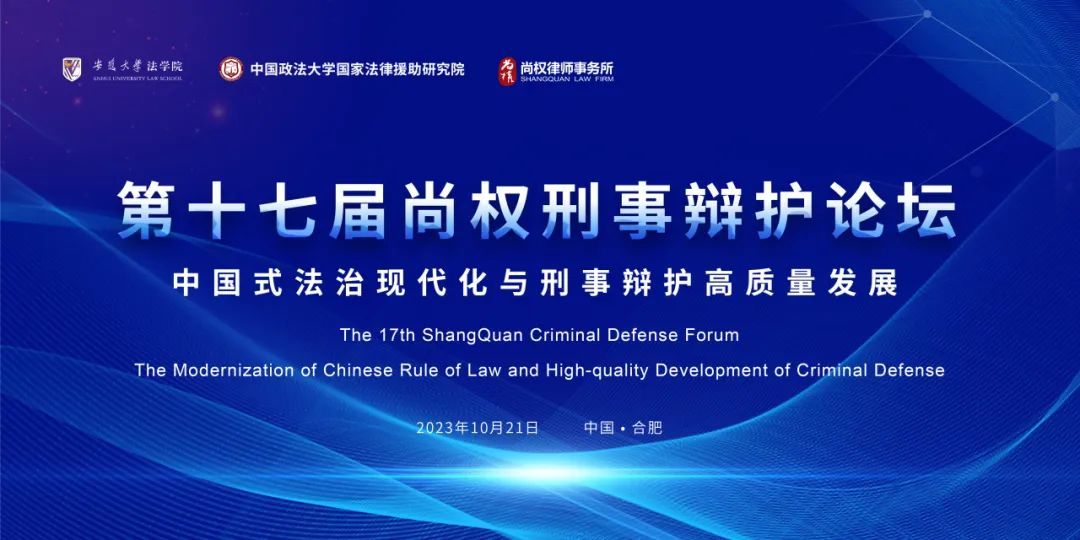
摘要
帮信罪刑事归责属性在共同犯罪、主从犯及罪名认定上不明确,带来了司法适用上的困境。帮信罪共犯问题与传统共犯立法体系冲突,实践中主从犯认定较为混乱,罪名认定呈现帮信罪“口袋罪”化趋势。帮助行为正犯化并未脱离共犯从属性,可在“双层区分制”共犯立法体系解决共犯和主从犯问题。需掌握帮信罪构成要件,厘清帮信罪与上下游犯罪的关系,方可准确界分罪名。
关键词:刑事归责属性;共犯;主从犯;罪名界分

陈羽枫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铁路运输检察院三级检察官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已完成了一代、二代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正处于实现三代网络的过渡时期。Web3.0时代的网络犯罪对传统刑法适用带来了挑战。作为新型网络犯罪,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设立,特别是2019年“两高”出台司法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以来,本罪打击数量呈几何级增长,为遏制网络犯罪发挥有效作用。相比之下我国相关理论层面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却相对落后,帮信罪的刑事归责属性存在较大争议,以致影响了司法适用。为此,学界和实务界必须妥善处理好帮信罪传统刑法教义学与实证的关系,以应对Web3.0时代的全面挑战。
新型网络犯罪的行为主体、行为方式、行为结果等均不同于传统犯罪,网络化的特征对传统刑法理论带来极大挑战。《解释》的出台,对帮信罪构成要件中争议较多的“情节严重”予以细化,赋予了帮助行为独立可罚性,解决了司法实践中标准不好把握的问题,但这些努力仅仅解决了帮信罪司法适用层面最紧迫的问题,本罪的刑事归责属性问题仍亟待处理。当前我国刑法中,帮信罪刑事归责属性存在理论和实务上的困惑。帮信罪刑事归责属性暂未厘清,立法上选择的帮助行为共犯化主流观点与刑法共犯从属性理论存在冲突,主从犯认定混乱。本文拟从实证角度出发,对帮信罪的刑事归责属性加以阐释。
二、帮信罪刑事归责属性的司法困境
(一)总体情况
本文以裁判文书网为数据来源,通过研究2021年帮信罪判例,展开刑事归责属性实证研究。本文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案由,检索到2021年刑事裁判文书19883份,按照2%的比例随机抽取400件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从空间分布看,样本涉及全国26个省份,排在前10位的省份有:河南54件,湖南47件,福建36件,广东31件,江苏30件,上海29件,广西23件,辽宁20件,江西17件,湖北16件。从时间分布看,裁判文书网中帮信罪近五年判例情况如下:2018年24件,2019年92件,2020年2700件,2021年19883件,2022年1-4月1978件。本罪案件数量自2020年大幅度上升,2021年接近2万件,2022年前四个月已接近2000件。根据正义网公布内容,2021年帮信罪起诉近13万人,同比上升超8倍,起诉人数排在危险驾驶和盗窃罪之后,成为全国第三大罪名。帮信罪案件量暴涨的原因如下:一是《解释》的出台,对本罪构成要件中的“情节严重”情况以列举形式予以规定,让司法部门有的放矢。二是2020年10月公安部“断卡”行动开展,加强对“两卡”犯罪打击力度,导致该罪数量大幅上升。三是实践中司法部门法律适用简单化,帮信罪成为新型“口袋罪”。
(二)刑事归责属性的困境
从定罪罪名上看,样本中共有400件732人被判处刑罚。其中,帮信罪393件697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6件19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1件5人,盗窃罪0件11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0件3人,诈骗罪0件3人,开设赌场罪0件3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0件2人,偷越国边境罪0件1人(含数罪并罚情况)。在实务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共同犯罪认定受限制
帮信罪属于网络犯罪链条下游犯罪的一环,与诈骗、赌博等罪名形成上下游犯罪关系。在涉及帮信罪与其他犯罪形成共同犯罪,存在竞合可能时,多数判决仅简单粗暴认定帮信罪,实质上架空了共犯的适用。如陈某某等帮信案,行为人本构成赌博罪的片面帮助犯,应与帮信罪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但判决中仅认定帮信罪。如黄某放等帮信案,行为人主动联系上游诈骗团伙,将上游犯罪所得赃款“洗白”,应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法院认定帮信罪。有判例统一按帮信罪论处,不考虑竞合犯情况。如康某伟帮信案,行为人充值“跑分”平台,使用支付宝账户为赌博平台既遂的犯罪所得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属本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竞合犯,法院只认定本罪。
2.主从犯认定分歧大
在样本中,委托辩护人的有168件,其中,就一般辩护内容辩护(认罪认罚、初犯、偶犯等)的162件,占比96.43%;就主从犯辩护的34件,占比20.24%。很大一部分案件中,辩护人以行为人属“从犯”为由从轻辩护。对于主从犯问题,在实务中争议很大。以数人贩卖银行卡或“跑分”帮助支付结算为例,有法院认定为共犯,详细区分主犯与从犯,如何某熠帮信案;有法院认为所起作用相当不宜划分为主从犯,如谷某磊等帮信案;有法院避重就轻,认为各被告人在犯罪中均积极参与,按照其各自所起作用进行量刑,因此可不区分主、从犯,如陈某等帮信案;有法院认为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如高某刚等帮信案;有法院认定各被告人均属上游犯罪的共犯,均起帮助作用,系从犯,如李某森等帮信案。仅上述一种情况,在法院的审判实务中就有数种认定共犯和主从犯的认定方法(尚不包括检察机关和律师意见建议),可见帮信罪主从犯认定比较混乱。
3.罪名认定不明确
在样本中,检法变更罪名46件,占比11.5%。可见,有1/9的案件在罪名认定上公检法三机关存在争议。但有393件判例认定帮信罪,认定其他罪名的仅有7件,帮信罪定罪率98.25%。通过分析个案可知,司法机关并未真正解决罪名认定争议问题,而是将一部分定性争议案件以帮信罪定罪,形成实质上的“口袋罪”。在司法实践中,个别法院因对帮信罪刑事归责属性界定不清出现案件定性错误问题。如景某臣等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帮信案,法院认定转卖他人银行卡给上游犯罪团伙构成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提供自己银行卡给上游团伙构成帮信罪。转卖他人银行卡表面上符合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构成要件,实际最终目的为帮助支付结算,应认定帮信罪一罪。
上述判例反映出司法实务三种倾向:一是共犯问题处理不合理。一部分判例并未对犯罪行为侵害的全部法益准确评价,简单以帮信罪定罪处罚,出现“漏罪”问题。对法益评价不全面直接造成公检法律对犯罪界定出现争议。二是主从犯问题冲突严重。主从犯认定分歧很大。三是实务中对网络犯罪性质界分不清晰。帮信罪上下游犯罪定性比较混乱,导致帮信罪“口袋罪”化处理,架空了“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作用。
三、帮信罪刑事归责属性冲突的实证分析
我国《刑法》将帮助行为独立于上游正犯单独设置帮信罪。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将存在理论争议的中立帮助行为提升为正犯处罚。在网络时代的司法实践中,与传统帮助行为不同的是,网络帮助行为可能没有正犯或难以抓获正犯,“而网络犯罪中的帮助行为已经完成危害性的超越和独立性的突破”,故应独立评价为正犯。也有学者认为,此举可能导致全面处罚中立帮助行为,妨害网络技术创新和技术经济发展,应予限缩适用。对于帮信罪的刑事归责属性在理论上争议较大,却未能解决实务中的诸问题。司法解释与理论冲突使办案人员在实践中无所适从。
(一)与共犯立法体系冲突
网络犯罪模式由传统“一对一”向“一对多”“多对多”转变,上游轻微违法行为经网络放大后可能产生更严重后果。网络匿名属性使网络犯罪呈现产业链式发展,共犯与正犯间可能没有意思联络,若按照上游犯罪认定帮助者为共犯,当帮助行为危害性大于正犯时,按传统共犯理论难以平衡犯罪构成与量刑。基于此,有学者提出这种归责路径,使帮助行为摆脱对正犯的依附作用,以应对网络共同犯罪现实挑战;将具有独立的帮助行为扩张解释为正犯,直接通过犯罪构成进行评价。这对我国传统共犯理论造成了冲击,甚至打破了“正犯—共犯”二元格局,动摇了整个共犯体系。本文认为上述观点过于激进,不适于采用,应从刑法教义学层面做合理解释。主流共犯立法体例包括单一制和区分制,以区分制的共犯立法模式为主导。德、日刑法共犯立法采区分制下的单层分类体例,将行为人区分为正犯、教唆犯、帮助犯,定罪量刑评价由重至轻。“正犯是共同犯罪定罪和量刑的中心,其不仅具有定罪的价值而且具有评价参与人刑罚轻重的功能——正犯是共犯的处刑基础,共犯按照正犯之刑处断或者减等处罚”。这种单层分类体系将犯罪分工与作用评价融为一体,却并未解决根本问题。我国实务中存在大量共犯认定和定罪量刑不匹配问题的案件,其根源在于司法工作人员知识结构老化,对我国共犯立法体系不清楚甚至仅依靠字面意思,“误打误撞”按照单层分类体例的思维方式处理共犯问题。在帮信罪实务中,一些法院往往忽略共犯问题只认定帮信罪,导致罪责刑不统一。如苏某鹏等帮信案,二被告明知“跑分平台”上的资金为网络诈骗、网络赌博资金,出租场地,管理他人“跑分”、资金转账,法院认定为帮信罪。行为人对深度参与上游犯罪,起主导作用,属上游犯罪共犯。
传统共犯理论与单层分类体系间的冲突影响德、日共犯教义学发展,正犯与共犯区分由形式标准向实质标准转变。“在实质客观说之下形成所谓共犯性为正犯化的逻辑结论存在明显的体系性弊端,为求得量刑的合理性而舍弃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换言之,按照德、日刑法共犯立法体系,共犯的量刑一定轻于正犯,面对网络犯罪共犯的法益侵害性大于正犯,这种共犯立法体系就造成了量刑上的不匹配。对于这种量刑不匹配问题,德、日采用在实践中对正犯进行实质化解释,将一部分侵害法益较重的共犯认定为正犯。日本学者西田典之认为,“为了处罚上的具体妥当性,而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明确性也许是被允许的”。与德、日不同,我国共犯立法体系采双层区分制结构。即对共犯人同时采用了分工分类(正犯、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和作用分类(主犯、从犯)两种不同分类标准。这种共犯立法体系的优势在于,分工分类标准与作用分类标准并行,即便依分工分类标准确定了正犯与共犯,也可以根据所起作用大小依作用分类标准评价为主犯与从犯,二者互不干扰,这样实现先根据分工分类标准区隔考量正犯或共犯,再根据在犯罪中所起作用区分主从犯,进行量刑匹配,可以解决量刑合理性与构成要件定型性之间的矛盾问题。
(二)主从犯认定冲突
通过上文可见,尽管在帮信罪主从犯问题成为律师辩护重要内容之一,但在理论研究层面却鲜有人问津。造成帮信罪主从犯认定乱象的根源在于理论的不明确。一是帮信罪的共犯理论问题。如上文所述,帮信罪共犯问题争议多年尚无各方满意的观点,主流观点帮助行为正犯化既存在逻辑不自洽之处,又无法衡平各观点间的矛盾,直接对司法实务造成影响,在判决中共犯和主从犯认定难以统一化。二是主从犯关注度问题。相对于共犯问题,网络犯罪主从犯研究热度很低。主从犯问题本不复杂,致使理论界并未将研究重点略加倾斜,但在司法实务中主从犯问题恰恰影响了网络犯罪的量刑问题。在上下游网络犯罪案件的起诉阶段和庭审阶段,主从犯问题已成为律师辩护的重要辩点,该问题常常为公诉人员、审判人员带来困扰。本文认为,我国刑法共犯立法采双层区分制体系,一方面根据分工分类方法对正犯和共犯加以区隔,另一方面根据作用分类方法对主从犯加以明确,二者互不干扰。这种双层区分制体系,可妥善解决主从犯认定难题。以帮信罪为例,该罪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属于共犯,在共犯中又可根据各犯罪人所起作用区分主犯或从犯,这种方式可以做到量刑与构成要件相均衡。对于认为帮信罪中办卡团队主谋为从犯的观点,本文认为,帮信罪中办卡团队主谋在办卡犯罪行为范围内当然属于主犯,以所造成的实际危害量刑,如果认为其属于整体犯罪链条中的从犯,则应当以整体犯罪链条的犯罪金额量刑,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罪名认定冲突
《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了帮信罪的6种行为模式,但仅规定了具体行为样态。《解释》对“情节严重”予以规制,并设置了其他情节严重情形条款,但未对被害人损失、侵害的法益予以明确。实务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网络犯罪各相近罪名区分不当,办案仅依条款定罪不考虑法益侵害。上述问题导致实务中帮信罪呈现“口袋罪”化趋势。在样本中,在移送起诉和庭审阶段罪名争议案件有46件,占比11.5%,未认定帮信罪的案件仅有7件,占比1.75%。委托辩护人案件168件,就犯罪定性辩护的仅9件,占比5.36%。可见实务中帮信罪定性后改变的可能性很小,律师就定性辩护率很低。上述原因使罪名本身的巨大争议被有意或无意忽视了。如黄某等帮信案,二被告明知上游正犯行为为网络赌博,仍加入并按上游要求非法提供实时转账服务,本属赌博罪和本罪的想象竞合犯,法院认定本罪。也有判例存在罪名争议,法院一律按本罪处理。如韦某克等帮信案,被告人组建办卡、“洗钱”微信群,统一组织人员办卡,为上游诈骗团伙提供对公账号,收购大量银行卡、电话卡、U盾,多次以隐藏方式邮寄给上游诈骗团伙用户实施网络诈骗。
四、帮信罪刑事归责属性的实证解释进路
(一)刑事归责属性的教义学立场
网络犯罪以其“一对多”“多对多”模式区别于传统犯罪,犯罪更为隐蔽,正犯与共犯之间意思联络趋弱,共犯的独立性更强。这种现状在实务中的直接体现为:正犯难以追查,甚至出现仅存在共犯的状况;正犯与共犯之间犯罪故意难取证,多数时候互相不认识,有时共犯甚至不知道上游正犯从事何种犯罪行为。如黄某兵帮信案等。我国在设立帮信罪时并未对该罪的刑事归责属性进行阐释,导致理论界在该问题上一直争议未定。“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积极盘活传统刑法规范,尽量把传统刑法规范适用于新型网络犯罪,出现了刑法解释的扩张化趋势”。“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帮助行为成立共犯,正犯应明确构成犯罪。在网络犯罪中,该学说难以解释无主观意思联络的共犯行为,而不得不以“片面的帮助犯”理论加以阐释。当面对“明知”上游正犯触犯A罪,实则上游正犯触犯B罪的情况(如申某帮信案等),则难以认定为犯罪。“限制从属性说”,认为正犯实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帮助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当面对上游正犯无法查明或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如冯某贤等帮信案等),帮助行为就不能构成犯罪。“最小从属性说”,认为共犯仅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将正犯违法性与共犯的成立进行切割判断。但该学说依然不能解决帮助犯具有独立地位的根本矛盾问题。“在纯粹违法而不犯罪的行为,由于完全不可能该当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此时就仍然无法入罪处理”。
本文认为,共犯正犯化与共犯从属性存在天然矛盾,试图加诸于共同犯罪理论上的“小修小补”,不仅无异于根本问题解决,反而弄巧成拙对共犯体系造成了破坏,因此本文坚持帮助行为正犯化立场,从实务角度提出如下看法:一是帮助行为正犯化不同于共犯正犯化。尽管帮助行为正犯化脱胎于德、日共犯正犯化理论,但与之相比仍存在本质区别:网络犯罪中存在被帮助者未达到入罪标准,而帮助者因“积量构罪”规则构成帮助犯,被帮助行为不构成犯罪,也就不存在正犯和共犯问题,帮助行为正犯化更符合司法实践要求,不应将帮助行为正犯化等同于共犯正犯化。二是在我国双层区分制共犯立法体系下解决问题。德、日建构于单层区分制共犯体系基础上的必经阶段是共犯正犯化,对于我国双层区分制共犯体系,不存在量刑与构成要件均衡问题。在实务中,对于网络犯罪案件的判断,应先根据行为性质进行区隔,确定属于正犯还是共犯,若符合诈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赌博等上游犯罪,对正犯其主要、引导作用,属于正犯;若符合帮信等下游犯罪构成要件,对正犯起次要、帮助作用,属于共犯。区隔正犯共犯后,再根据具体侵害的法益确定罪名,并根据作用分类明确主从犯。在我国双层区分制共犯立法模式基础上,此种方法妥善处理了犯罪构成与量刑的冲突问题。三是帮助行为正犯化区别于传统共犯理论。帮助行为正犯化难以融入传统共犯理论,争论至今未有解决办法,使实务工作者无所适从。实务中大量案件办理时并未就是否构成共犯问题作过多纠结,反而在上下游罪名界定和帮助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上存在很大争议。部分法院对此类问题避而不谈,认定帮信罪,如李某水等帮信案、黄某等帮信案等。为便于解决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同意学者江溯的观点,承认帮助行为正犯化不属于传统共犯范畴,可研究该行为本身的独立可罚性问题。我国设立帮助行为正犯化本质上仍属于共犯范畴,只是为了满足打击网络犯罪抓获难、取证难问题所做的一种法律拟制,这种法律拟制可简化诉讼过程,有助于国家高效打击网络帮助行为,对于帮助行为本身的共犯性质并未产生影响。
(二)刑事归责属性的主从犯认定
通过上文可见,尽管在帮信罪主从犯问题成为律师辩护重要内容之一,但在理论研究层面却鲜有人问津。造成帮信罪主从犯认定乱象的根源在于理论的不明确。一是帮信罪的共犯理论问题。如上文所述,帮信罪共犯问题争议多年尚无各方满意的观点,主流观点帮助行为正犯化既存在逻辑不自洽之处,又无法衡平各观点间的矛盾,直接对司法实务造成影响,在判决中共犯和主从犯认定难以统一化。二是主从犯关注度问题。相对于共犯问题,网络犯罪主从犯研究热度很低。主从犯问题本不复杂,致使理论界并未将研究重点略加倾斜,但在司法实务中主从犯问题恰恰影响了网络犯罪的量刑问题。在上下游网络犯罪案件的起诉阶段和庭审阶段,主从犯问题已成为律师辩护的重要辩点,该问题常常为公诉人员、审判人员带来困扰。本文认为,我国刑法共犯立法采双层区分制体系,一方面根据分工分类方法对正犯和共犯加以区隔,另一方面根据作用分类方法对主从犯加以明确,二者互不干扰。这种双层区分制体系,可妥善解决主从犯认定难题。以帮信罪为例,该罪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属于共犯,在共犯中又可根据各犯罪人所起作用区分主犯或从犯,这种方式可以做到量刑与构成要件相均衡。对于认为帮信罪中办卡团队主谋为从犯的观点,本文认为,帮信罪中办卡团队主谋在办卡犯罪行为范围内当然属于主犯,以所造成的实际危害量刑,如果认为其属于整体犯罪链条中的从犯,则应当以整体犯罪链条的犯罪金额量刑,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刑事归责属性的罪名边界划分
样本中移送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变更罪名的案件有46件,占比11.5%。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案件定性存疑,公检法律四家意见“统一”的情况。帮信罪上下游网络犯罪由于共犯和刑事归责属性尚未厘清等原因,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存在罪名争议。
1.帮信罪与诈骗罪
二者构成要件存在较大差别,比较容易区分,诈骗罪为侵犯财产法益的犯罪,属网络犯罪链条中的上游犯罪,共同犯罪中的正犯范畴,而帮信罪为侵害社会管理秩序中的网络管理秩序法益犯罪,属网络犯罪链条中的下游犯罪,共同犯罪共犯范畴,二者之间存在法益区隔,通常不容易混淆。除非帮信罪行为人与上游诈骗团伙已经形成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深度参与上游诈骗行为,与上游诈骗行为形成固定犯罪链条。实务中将二者混淆的案件,通常情况是个别公安机关错误的认为提供“两卡”为上游“洗钱”的帮信罪行为人既然“明知”上游为诈骗,并提供帮助,即可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而移送审查起诉(如姜某鸽帮信案、朱某帮信案等)。此类看似荒谬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很常见,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离。一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只适用于共同正犯,帮信罪因属共犯不适用,更何况实行的是全部“责任”而非全部“罪名”,这种做法明显混淆了定罪与量刑。二是主观归罪是司法办案的沉疴,若不及时解决,容易产生冤假错案,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侵蚀司法机关公信力。
2.帮信罪与掩隐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属于赃物犯罪,在构成要件上与帮信罪存在相近之处,即转移资金。二者区别在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需要明知资金来源为犯罪所得,换言之,行为人明知上游资金为犯罪既遂后的赃款。帮信罪则为明知上游资金来源于犯罪,却并不知道是否为既遂后的赃款。实务中部分司法机关在定罪上存在争议。如韦某华等帮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原审法院因被告明知上游为犯罪所得,通过挂失取现,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二审法院认定盗窃罪,认为并非明知网络诈骗所得及收益,原审法院定性错误。本文认为,应当根据本案其他证据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上游为概括犯罪后的赃款,如果可推断明知,则构成想象竞合犯。也有法院对两种罪名界分说理比较充分,如阮某勇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帮信案,法院认为被告人阮某勇被他人带到宾馆看守,且在同一天有大量的款转入其账户,并在他人监督下随即划转到指定的其他账户,其应当明知多次转入其银行卡的钱是电信网络诈骗所得,但仍协助支付结算,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诈骗罪与掩饰罪
前者为上游犯罪的正犯行为,后者为下游赃物犯罪,也属于正犯范畴,后者与前者接触较为紧密,明知上游诈骗行为既遂后,帮助“洗钱”。后者如果深度参与前者的诈骗过程,对诈骗行为起到支配作用,并与上游诈骗团伙形成长期、稳定、密切配合的关系,也可认定为诈骗罪。两种犯罪边界区分不明显,需要结合个案犯罪事实等综合判断。本文认为,实务中上述方法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明知上游为诈骗犯罪,参加上游诈骗团伙,与之形成密切配合关系,长期为上游诈骗团伙提供“两卡”或转账取现的,可认定为诈骗罪。二是出售“两卡”后,明知流入资金为既遂的犯罪所得情况下,又代为转账取现或者为转账提供刷脸验证的,可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三是明知上游犯罪,仅提供“两卡”,未实施其他行为的,可认定为帮信罪。此外,因赌博罪与诈骗罪均属犯罪链条中的上游正犯,固上文对诈骗罪与其他罪名的处理方法参照适用于赌博罪,此处不赘。
4.帮信罪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帮信罪保护的法益是网络管理秩序,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保护的法益是信用卡管理秩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的法益是个人信息管理秩序,三者交叉地带存在争议。在网络犯罪中,妨害信用卡管理行为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均可以作为帮信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可以说二者的构成要件与帮信罪的预备行为发生重叠。因此在立法中,贩售“两卡”数量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均成为帮信罪情节严重类型的衡量标准之一。二者之间界分较为明晰,二者与帮信罪的界分需要详细阐释。在帮信罪案件办理过程中,应当做实质解释,收购“两卡”和“个人信息”如果只是犯罪前端,实质目的在于帮助上游犯罪“洗钱”,应认定帮信罪,而不能仅以前端预备行为认定犯罪。对于“卡商”出售“两卡”和“个人信息”行为,可根据具体案情、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分别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实务中,此类案件定性五花八门。有认定数罪并罚的,如王某明等妨害信用卡管理案,被告人收购银行卡转卖他人用于为上游犯罪团伙“洗钱”,同时收购银行卡直接为上游诈骗团伙“洗钱”,法院认定帮信罪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数罪并罚。也有认定帮信罪的,如陈某豪帮信案,法院认为无论是出售自己的银行卡还是他人的银行卡,其行为本质都是帮助他人接收、流转上游网络犯罪的赃款,在刑法意义上属于同一种行为,原审判决将出售自己的银行卡和出售他人的银行卡认定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以两种罪名定罪,适用法律错误。可见,努力厘清各罪之间边界,妥善处理共犯问题对于网络犯罪正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5.帮信罪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二者存在混淆的案件类型主要集中于非法引流帮助类型的犯罪。前者将“帮助”行为单独入罪,后者将“上网”行为单独入罪。前者着力点在于全面辅助正犯实施犯罪,而后主要行为类型为建设群组网站和发布虚假信息,相对范围较小。后者属于前者的前端行为之一,前者的规制重点主要为支付结算服务、广告推广等,前者的设立目的为了解决共犯相关问题。相比较而言后者属于特殊罪名,当二者混淆无法识别清楚时,应优先适用特殊罪名,即后者。但通过样本可见,提供广告推广、引流案件12件,均以帮信罪定罪,无一认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信罪成为“口袋罪”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取证简单。
五、结语
在Web3.0时代,网络犯罪的发展已脱离传统犯罪理论框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设立是网络犯罪罪情演变的立法回应,是刑法为强化对网络犯罪打击力度,维护国家网络安全的积极尝试。通过对帮助行为正犯化理论梳理和实证解释,达到妥善厘清刑事归责属性,准确界分本罪与其他罪名之间界限的目的,实现既有效打击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又为技术经济发展预留空间,推进国家网络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李怀胜:《三代网络环境下网络犯罪的时代演变及立法展望》,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4期,第94页。
[2]刘艳红:《Web3.0时代网络犯罪的代际特征及刑法应对》,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5期,第100页。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颁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9年11月1日施行)第十二条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二)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三)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四)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五)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六)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5]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1)闽0212刑初349号刑事判决书。
[6]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人民法院(2021)桂1029刑初278号刑事判决书。
[7]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2021)湘0503刑初458号刑事判决书。
[8]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21)闽0304刑初787号刑事判决书。
[9]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21)云0402刑初559号刑事判决书。
[10]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晋05刑终148号刑事判决书。
[11]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民法院(2021)黑0221刑初194号刑事判决书。
[12]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湘03刑终391号刑事裁定书。
[13]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21)云0103刑初1496号。
[14]参见车浩:《刑事立法的法教义学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载《法学》2015年第10期,第12页。
[15]参见刘艳红:《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流变及批判——以德日的理论和实务为比较基准》,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5期,第41页。
[16]参见刘艳红:《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之批判》,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第19页。
[17]参见于志刚:《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120页。
[18]王霖:《网络犯罪参与行为刑事责任模式的教义学塑造——共犯归责模式的回归》,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9期,第33页。
[19]转引自钱叶六:《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6页。
[20]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法院(2021)桂0512刑初122号刑事判决书。
[21]阎二鹏:《共犯行为正犯化及其反思》,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06页。
[22][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日]西田典之:《共犯理论的展开》,江溯、李世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23]参见钱叶六:《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7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第2款,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5]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湘02刑终222号刑事判决书。
[26]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桂1228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书。
[27]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21)赣1002刑初387号刑事判决书。
[28]欧阳本祺:《论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限度》,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第167页。
[29]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14页;黎宏:《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页;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页。
[30]湖南省洞口县人民法院(2021)湘0525刑初506号刑事判决书。
[31]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2021)赣1027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
[32]参见张明楷:《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第14页。
[33]王昭武:《共犯处罚根据论的反思与修正:新混合惹起说的提出》,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第240页;王霖:《网络犯罪参与行为刑事责任模式的教义学塑造——共犯归责模式的回归》,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9期,第33页。
[34]于志刚:《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探索与理论梳理——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法定位为角度的分析》,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3期,第86页。
[35]参见王华伟:《网络语境中的共同犯罪与罪量要素》,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2期,第77页。
[36]本文所选400件判例中,委托辩护人案件168件,仅有1件案件辩护人就是否构成共犯辩护,有51件案件在犯罪定性方面存在争议和界定不清等问题。
[37]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刑终480号刑事判决书。
[38]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湘02刑终222号刑事判决书。
[39]参见江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解释方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5期,第84页。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第2款,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41]河南省唐河县人民法院(2021)豫1328刑初725号刑事判决书。
[42]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2021)豫0223刑初658号刑事判决书。
[4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桂12刑终200号刑事判决书。
[44]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宁明县人民法院(2021)桂1422刑初181号刑事判决书。
[45]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2021)湘0422刑初298号刑事判决书。
[46]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湘01刑终1262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