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权律所 时间:2024-0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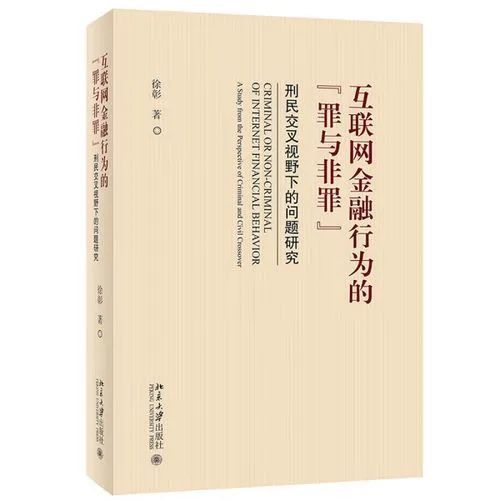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给金融创新和金融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一系列风险,尤其以非法集资犯罪为甚。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彰博士在《互联网金融行为的罪与非罪——刑民交叉视野下的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互联网金融并非简单的传统金融业务互联网化,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互联网+金融”,而是一种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徐彰:《互联网金融行为的罪与非罪——刑民交叉视野下的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2022年版,p3。以下简称为“徐彰书”)这一点,笔者完全赞同。笔者认为,金融创新是指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金融创新本质属性在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是为了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以及大众投资理财的需求。很多互联网金融创新既背离了金融的本质,也背离了金融创新的本质。一些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就是“玩资金”“圈钱”,属于“圈地运动”式运作,既没有技术上的创新,也没有要素组合上的创新。很多民间小额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甚至的讨债公司,换个“马甲”就玩起了互联网金融创新,其目标不是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更不是满足实体经济、创新创业的资金需求,异变为“圈钱”运动(李勇:《互联网金融乱象刑事优先治理政策之反思》,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一、关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治理
互联网金融犯罪作为经济犯罪,其治理对策具有特殊性;刑法中关于金融犯罪的罪名属于行政犯,也具有特殊性,这种双重特殊性决定了刑事政策、立法和司法上都需要处理好鼓励金融创新与防控金融风险之间的平衡。徐彰博士对传统犯罪治理模式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直接套用进行了反思。
金融属于市场行为,属于经济活动中的分配环节,其治理对策必然要受市场原理的制约。市场经济强调市场的作用,根据市场原理主义,最佳策略就是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来解决市场中的问题,政府尽量减少干预。但是这种绝对的市场自由主义也是有问题的。市场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不可避免地出现越轨行为,需要规制和调控。这种两难境地决定了治理对策就是要平衡市场与干预之间的关系。日本学者齐藤丰治对如何治理企业越轨行为概括出四类方法:(1)根据市场原理,通过市场竞争对不良企业进行淘汰和重新“洗牌”;(2)依据企业的自主规制,构建内部治理机制,制定和实施合规计划;(3)强化市场监管机构的制裁,特别是扩大课征金的适用;(4)通过刑事制裁来解决。这四种方法并非对立排斥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并存关系(【日】齐藤丰治:《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刑法》,载魏昌东、顾肖荣主编:《经济刑法》第1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0页)。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违法行为的治理策略,偏重于刑事手段。徐彰博士对此提出了反思,运动式执法表面上解决了实践中最紧迫的问题,保护了受害人的财产,但实质上并未从根本上治理互联网金融乱象(徐彰书p20)。从德国和日本经济犯罪治理经验看,行政罚款在经济犯罪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在1977年《反垄断法》中引进课征金(相当于行政罚款)制度以前,刑事手段在经济犯罪领域是唯一手段,但是其副作用也极为明显。为改变这一不良现状,最终构建起以课征金为中心,包括解散命令、取消批准注册、停止营业、强制调查、处理劝告等在内的行政制裁体系。德国的秩序罚同样在经济刑法领域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德国经济刑法理论中,犯罪行为与违反秩序行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违法行为。对违反秩序行为适用罚款与对犯罪行为判处罚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司法活动,前者不作为前科登记。市场原理原本就是我们的弱项,企业合规计划在国内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行政监管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空白和盲区甚多。由新华社《金融世界》、中国互联网协会联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金融报告(2014)》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互联网金融诸多业务在法律法规方面存在大量的空白,P2P网贷平台及股权众筹等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监管主体、准入机制、业务运转流程监控、资金及其孳息监管处理方式等还不明确。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经济创新模式,应当在适度发挥市场原理和企业自主规制作用的同时,当务之急就是完善行政规制的法律规范体系,强化行政监管,鼓励创新与规范引导并行,这才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应有之意。因为“相对于建立一个全面的行政法体系包含行政法规与行政措施而言,将经济违法行为比如在电子数据处理领域予以犯罪化而形成的国家干预,可能会对个人自由造成更少的侵犯。”(【德】克劳斯·梯德曼:《德国经济刑法导论》,周遵友译,载《刑法论丛》2013年第2卷。)只有在严重背离市场原理,严重侵害法益,行政处罚不足以规制时,比如打着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幌子实行诈骗、设置“庞氏骗局”等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刑法才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应当是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经济越轨行为刑法治理的限度。
二、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罪与非罪认定
徐彰博士指出,互联网金融犯罪属于行政犯,同时又与民商法交叉,呈现行刑交叉、刑民交叉的特点。比如P2P网络借贷本质上是民间借贷,受民法的保护和调整,股权众筹本质上是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具有民法属性(徐彰书p39/143)。
1.就行政犯这个特点而言,在认定罪与非罪过程中需要把握行政从属性。关于行政犯,历来存在从属性与独立性之争。行政犯的从属性是指行政犯成立及违法性的判断依附于行政法的规定,又称行政从属性。在立法上的直接体现是空白刑法,罪状的判断有赖于行政法规之补充。按照功能划分,可以分为构成要件之行政从属性和违法阻却事由的从属性,前者是刑法构成要件的判断需要依照行政法的规定,后者指因行政机关的核准、允许而阻却违法;按照从属的规范可以分为行政法规范的从属性和行政处分的行政从属性,前者指刑法构成要件需要依赖于行政法规来补充,后者指行政犯的成立以受过行政处分为前提,如我国刑法中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以行政机关责令支付拒不支付为条件。“行政法的制裁规定中若以刑罚为法律效果的罚则条款,即属附属刑法,而与主刑法同样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这些附属刑法若以空白刑法的立法方式而为规定者,则有待行政命令或规章或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等的补充,才能具体运作,故使这些规定与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具有行政从属性”。(林山田:《刑法通论》(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0页)独立性说认为犯罪行为是刑法的特有现象,行政违法行为及行政处罚与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本质不同。按照戈尔德施密特的观点,行政刑法应当独立于司法和刑法,行政犯仅侵害公共秩序。行政法,只是认定犯罪的线索,是否构成犯罪须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条文的具体规定与目的,进行独立判断,包括构成要件的独立性、事实认定的独立性和处理结论判断的独立性(参见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 理念、方法与路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 期。)笔者认为,从属性与独立性之间具有阶层递进关系,先进行构成要件从属性考量,再进行违法性的独立性判断(李勇:《互联网金融乱象刑事优先治理政策之反思》,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笔者的观点与徐彰博士的观点一致,徐彰博士指出“行政犯的犯罪构成前提要件是违反行政法规,即行政犯必然存在双重违法性,一是行政违法性的判断,二是在具备行政违法性基础上进一步作出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徐彰书p59)。
关于实质违法性的判断,徐彰博士主张实质判断来识别侵害的法益。对于传统观点金融犯罪的法益界定为金融管理秩序,徐彰博士进行了解构和重构,他认为应将金融管理秩序解构为金融安全与金融消费者的资金安全,其中前者为附随法益、超个人法益,后者为核心法益、个人法益,互联网金融犯罪“罪”与“非罪”的判断应落脚于后者(徐彰书p95-112)。笔者对此高度认同。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说,秩序法益具有抽象性,应当将秩序这个集体法益还原为具体的个人法益,否则容易导致机械司法。这一点不仅在互联网金融犯罪领域,在其他行政犯领域也如此。比如,陆勇案,如果单纯从秩序法益的角度看,似乎侵害了药品管理秩序,但是药品管理秩序还原为个人法益就是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身体健康法益,但陆勇的行为有益于癌症患者的身体健康,可见实质上并没有侵害法益,不具有法益侵害性,不构成犯罪。
2.就与民法交叉这个特点来说,民法免责事由具有阻却犯罪成立的空间。在民法中,自甘风险属于民法免责事由,为刑法中的“危险接受理论”所吸纳。在互联网金融犯罪中,受害人存在过错的,根据受害人是否具有专业的金融理财知识和投资经验,区分为自愿参与犯罪与非自愿参与犯罪,前一种情形受害人自行承担责任,甚至有可能成为共犯;后一种情形,受害人过程则可能导致犯罪人责任的减轻(徐彰书p113-132)。从民法的角度来说,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的界限,需要重新思考。徐彰博士认为,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关键在于分辨行为人所为的使表意人产生错误认识并由于这种错误认识进行的对自身权利的处分的诈骗行为,是针对合同进行的,还是通过合同针对财产本身进行的,前者有意思表述而后者没有。简单地说,民事欺诈的目的是合同,而刑事诈骗的目的是财产。民法关于欺诈的规定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决定的自由,而刑法规定诈骗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财产。换言之,就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针对合同本身还是以合同为手段指向财产(徐彰书p49-53)。上述观点,对于司法实践认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